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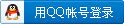
×
星子小人物的日常人生(连载)(完结篇)
本故事纯属虚构(原创) 游走的画笔
题记;每个人的生命来到这世界都是高贵的,即使人生有时候要卑微到尘土里,也要笑对生活,也许你身边就有一群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小生活,而,你我,皆是小人物!正因为小人物的生活才装点成了这个缤纷的世界。 滚 金 滚金究竟哪一年生我不清楚,滚金何时死爹,何时死的妈我更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他是个父母双亡的孩子,兄弟三人分得父母留下的’祖业”说是祖业,其实就是三间瓦房,外搭一间土胚灶房。滚金上面的两位兄长其中的二哥因为读书努力早些年考取了外地学堂,后就留在那个地方工作生活,结婚生子了。也许父母早亡故的原因,回来心里又没个着又没个落,滚金二哥有时候几年才带上城里的时髦媳妇回老家一趟。看一看,也只是看一看父母留下的破败的老房子,里面站一站也只是站着回忆一下里面的老时光。然后匆匆赶回自己的现代城市.没说要自己名下的那间老房,也没说不要。
滚金的大哥也喝过几年墨水,却没能走出去,而是在一所村小学做代课老师,这一“代”就代了30多年。也没能转个正。娶了本村姑娘,姑娘都快熬成了婆,里里外外的农事都是滚金大嫂操持.滚金大嫂算是很会操持,推到了父母留下的半边宅子,垒起了三层小洋楼,只剩滚金住的半边瓦房,
滚金的名字还是算命先生取的,那时候小孩出生,都兴起八字,算命先生说滚金八字硬有刑克,为了避刑克,命里又缺金,所以就取名滚金。但是滚金还是克了父母,这话是村上了年岁的老人说的。滚金从小个不高,长到十八岁也没长超1.6,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皮肤越长越黑黝,身材越长越敦实,越发显的矮了。滚金到了说媳妇的岁数,没能说上一门媳妇,为什么呀,没哪家姑娘愿意啊,一是姑娘们嫌弃滚金长的矮不说,还一口龅牙,穿个西装能当长大褂,,滚金又没有妈,姑娘心里都盘算如果另一半有个妈可以帮着料理家事照料小孩,比起婆媳矛盾带来的实惠强多了。现在的姑娘都精着呢,虽然不喜欢和婆婆呆在同一个屋檐下,可又希望婆婆全日照看自己的小孩料理自己的家务,自己可以腾出更多的私人时间和老公过二人世界。上上班,玩玩乐当然不中意滚金这种没妈家庭。其实没妈没貌都不是滚金的错,错就错在滚金只有爸妈那继承下来的瓦房,而且名下只一间,你说一间就一间吧,如果滚金能有门手艺勤奋一些,其实也可以把这间瓦房推倒做成大哥家一样排场敞亮的房子,可偏偏滚金学的艺是“国粹-麻将”。
滚金打麻将的场所,就是村上翠兰嫂子开的那家“翠兰便民店”翠兰嫂子五十开外,为人随和,也特爱打麻将。每天把店里那张用来打麻将的四方木桌收拾的干干净。不放任何杂物在上面,生怕放了别的东西会把那四方桌子压蹋似的,就连摆在桌子旁的四条长木凳也被抹的纹理越发清晰了等着麻友们入座。其实麻友无非是些上了岁数的老头老奶,打子儿的,也就是“一牌”一毛,或两毛钱的。通常一场牌局最后算子儿输赢下来很难超五十元的那种,用来打发时光的,当然有时候也有年轻人来玩,那也是一时兴起,但很少,也就是下雨天。或刚结婚生孩子的小媳妇之类因为三缺一被拉来’凑脚’。这些麻脚们,滚金是常脚。滚金打麻将有一习惯,就是爱“端架子”明明自己非常想打麻将就非要人请,叫。不叫几次是不来,其他三个等的着急催上见催人才慢慢騰騰的生怕踩死了蚂蚁般来。那时候没有移动电话这般方便,每次都是翠兰嫂子上他家去请人才来。好在他家离便民店不远,也就后方隔个七八栋房屋的样子。滚金两只脚还没踏齐翠兰嫂子家的操场。那些在门前沟里洗好衣服的喜欢待在便民店里歇一下脚的家庭妇女们就打趣起滚金来
滚金啊,你又来的这晚,是不是昨夜又上仿古街啦,早上爬不起来?还是屋里藏着了个漂亮姑娘,不舍得出门特?
别乱说,我还是个闺崽的,你们莫败坏我的名声撒,没姑娘跟我,到时候就上你们屋里吃饭去,总是乱说,这么关心我生活,又不介绍姑娘给我,打牌,打牌,开始坐好撒。滚金边说就边往牌桌上走。对于那些三姑六婆打趣话语也从不放心上,也不恼,也许是这么大年纪没找上个老婆,习惯了那些打趣的言语。显得很宽厚。可是上了牌桌,开战了就收起了那些所谓的宽厚杀得个风声水起。毫不留情,什么筒子万子饼子,不要的通通像小孩子扔石子样,扔到牌堂子里。自己不是摆一条龙就是赶清一色的牌型。滚金很会掐牌,明明手上不要的红中,白板,就是不撒手,就是拿捏着不打出去,而是打万子,筒子头脚没配上对的,嘿嘿。可是那些老头老奶才不管滚金的那些小精明呢,都闷着头打自个的牌,不要的统统扔掉,什么新张不靠边的又多远扔多远,见牌就碰,见牌就糊。每次轮到滚金还没伸手抓牌,下方就喊碰。碰。一圈下来个各滚金碰的头眼冒花。旁边好事者这时又开始打趣滚金:滚金啊装精了吧,这些老头老奶可不按你的设计出牌,哈哈,你越拿捏章法,人家乱打,不按你的章法出牌,越胡牌往往一上午滚金没捞着好处最后反输了好多子,也能输个20,30元钱,。。。。
滚金每次输的一个子也没有,你说他打牌精吧,可每次不是老头老太太的对手,为什么啊,因为滚金打牌是厉害的,也装聪明,会掐牌,可那些老头老太太,哪管这些啊,他们打牌抓牌出牌都不看场子里的,眼睛只顾自己抓的牌,东扯西扯,拉顺了就可,见牌就碰,见口就糊,所以就是赌王来了也不见得是这些老头老太的对手,只有输的多,赢的少,今天照样,滚金又输了。看着牌桌上散落的“子儿”,喉结动了动,没吭声。翠兰嫂子递来一杯凉白开:“要不今天就到这?张老头也该回家给浑家做饭了。”
他接过杯子,指尖碰着杯子的凉意,才缓过神来,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裤兜:“走了。”刚迈出门,就撞见大哥家的小儿子背着书包往村头跑,看见他就喊:“三叔,我爸让你今晚去家里吃饭,我妈炖了鸡汤!”
滚金脚步缓了缓,含糊应着“知道了”,却没往大哥家的方向走。他绕着村道慢慢晃,路过村东头那片刚搭起钢架的养鸡场,李老板正指挥工人卸饲料,看见他就喊:“滚金,上次跟你说的活,还考虑不?管吃管住,一个月三百!”
他摆摆手,加快了脚步。其实他不是不想去,那天从养鸡场回来,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甚至摸出了藏在床板下的旧瓦刀——那是年轻时跟瓦匠学活时留下的。可第二天一早,听见翠兰嫂子在门口喊“三缺一”,脚还是不由自主地往便民店挪。
回到那间瓦房,推开门就是一股霉味。他摸黑打开灯,昏黄的灯泡晃了晃,照亮了墙上贴着的旧日历,最新的一页停在三个月前。桌上放着半碗没吃完的咸菜,还是前几天大嫂送来的。他从柜子里翻出一包过期的北京牌方便面,刚想煮,门外就传来村东王麻子媳妇的声音:“滚金,在家不?”
他赶紧把方便面藏起来,开了门。王麻子媳妇手里拎着一篮青菜:“刚从菜园摘的,给你拿点。对了,前几天跟你说的邻村那个姑娘,人家问你啥时候有空,见个面?”
滚金挠了挠头,耳尖有点发烫:“姐,我这条件……还是算了吧。”
“啥条件不条件的?人家姑娘说了,就想找个实在人。你别天天在牌桌上耗着,好好跟人聊聊,说不定就成了!”王麻子媳妇把青菜塞给他,一扭一扭的走了。
关上门,滚金看着篮子里绿油油的青菜,突然觉得鼻子发酸。他把青菜放在桌上,又摸出那包方便面,拆开调料包,却没放水——他想起小时候,娘也是这样,把青菜切碎了煮面,还会卧个荷包蛋在里面。
夜里,滚金没开灯,坐在门槛上抽烟。远处传来大哥家的电视声,还有小孩的笑声,顺着风飘过来,又慢慢散了。他抬头看天,星星稀稀拉拉的,像牌桌上没凑齐的“对子”。
第二天一早,翠兰嫂子又来叫他打牌,他却摇了摇头:“不去了,我把屋收拾收拾。”他翻出扫帚,把屋里的灰尘扫了个遍,又把发霉的被褥抱到院子里晒。太阳晒在被褥上,散发出旧棉花的味道,混着阳光的暖意,倒让这破屋有了点生气。
中午,他煮了碗青菜面,加了点大嫂送来的腊肉,吃得干干净净。下午,他揣着仅有的几十块钱,去镇上供销社买了袋新的洗衣粉,还顺便给张老头带了包烟——上次打牌,张老头总把自己的烟递给他抽。
回到村里,他先去了便民店,把烟递给张老头:“叔,谢你上次的烟。”张老头愣了愣,笑着接过:“你这小子,还记着这事。”翠兰嫂子凑过来:“今天不打牌了?”
“不了,”滚金靠在门框上,看着远处的稻田,“明天我去养鸡场看看。”
那天晚上,滚金睡得很沉。他没梦见麻将牌,倒梦见了小时候,爹娘带着他和两个哥哥在院子里晒谷子,阳光把谷子粒晒得金灿灿的,他抓着一把谷粒,就往哥哥们身上撒,撒完就跑。哥哥们则放下爬谷的工具就追,追着滚金边叫娘,救他。娘则笑着直起腰用衣角抹了抹汗,眼睛里满是暖意望着三个儿,追逐打闹,太阳把娘四个照的更加明亮:娘...
第二天一早,他揣着瓦刀,往养鸡场走。路过大哥家时,大嫂正站在门口,看见他就喊:“滚金,去哪啊?”
“去养鸡场干活。”他停下脚步,难得挺直了腰板。
大嫂眼睛亮了亮,转身进屋拿了个布包:“这里面有件新衬衫,你大哥穿不上了,你拿去穿。干活别太累,中午记得吃饭。”滚金接过布包,指尖碰着布料的柔软,喉咙又发紧了。他点了点头,没说话,大步往养鸡场走。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过便民店时,他看见翠兰嫂子和张老头正朝他挥手,他也挥了挥手,脚步没停。
养鸡场的活确实累,搬饲料、扫鸡舍,一天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可晚上躺在养鸡场临时搭的板床上,他却觉得踏实——手里的老茧磨得发烫,却比在麻将桌上攥着“子儿”时,更有分量。
偶尔歇工的时候,他会回瓦房看看。晒过的被褥没了霉味,桌上摆着大嫂送来的咸菜和馒头,墙角堆着他从山上砍来的柴火。有时候王麻子媳妇还会来跟他念叨:“那姑娘还问起你呢,要不抽空见一面?”他还是笑着摆手,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局促——他想再攒点钱,把瓦房的屋顶修一修,把院子的篱笆扎起来,再买点新家具。
有次下雨,他从养鸡场回来,看见瓦房门口放着一把伞,伞下压着张纸条,是大哥写的:“屋顶漏雨,我找了人帮你补了,晚上别忘关窗。”他握着纸条,站在雨里,看着屋顶新铺的瓦片,突然觉得,这日子虽然没盼来媳妇,却也慢慢有了暖意——就像那漏雨的屋顶,补上了,就再也不怕风吹雨淋了。
后来,滚金在养鸡场干得越来越稳,李老板给他涨了工资,还让他管着鸡舍的日常。他把瓦房重新翻修了,换了新的门窗,院子里种上了王麻子媳妇的菜苗。每天下工,他就坐在院子里劈柴,或者给菜苗浇水,偶尔也会去便民店坐会儿,却不再上牌桌,只跟张老头、翠兰嫂子唠唠嗑,听他们说村里的新鲜事。
有天傍晚,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看见夕阳把屋顶的瓦片染成了金色,像撒了一层碎金子。他想起算命先生说的“命里缺金”,突然笑了——原来不是缺金,是他以前总想着从牌桌上“滚”出金来,却忘了,踏实过日子,手里的每一分钱,院里的每一棵菜,屋顶的每一片瓦,都是他的“金
|  | 本站法律顾问:易胜华律师|手机版|小黑屋| 尚庐山(原星子网)
| 本站法律顾问:易胜华律师|手机版|小黑屋| 尚庐山(原星子网)